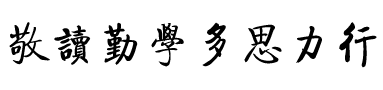作者:梁漱溟
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语
适之先生此信,重申其前旨,别无重要提示;且许我们,“将来一定要详细作答”;则此时殊无可以置论者,故我即不写答论。
前次张崧年先生在师大讲演,谓我与适之先生向来常常对垒互骂;而我在师大讲演“中国怎样才能好”,是对适之先生在北大讲演骂我之一“回敬”。此全与事实不符。就往事言之,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。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;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,乃在十二年春初发表于《努力周刊》,相隔一年余。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我者,而作答论,则已是十二年冬间,相隔大半年矣。此其间似尚没有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。就眼前事言之,则适之先生在北大讲演,怎样骂我,如果不是看见张先生演词中说到,我尚不知有此事;即至今我仍不悉其内容。指我讲演为对适之先生一“回敬”,果从何说起?今观适之先生此复,态度很好,益觉张先生于两方面均失言!
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,非平心静气以求之,必不能曲尽其理。若挟意气说话。伤个人感情事小,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;言词纠纷,亦乱读者耳目。罗素最佩服中国人的“平和气(pacific temper);我想适之先生与我,都不致十分失却中国人的态度。如果适之先生能给我们很详细的答复,我一定小心勉励着以此态度而讨论中国问题。——我前请教适之先生的信,虽没有冒犯的话,然不免气盛了些。
梁漱溟。十九,八,十六。
《村治》1卷5期,1930年8月16日。
附:
胡适之先生复信——答梁漱溟先生
作者:胡适
漱溟先生:
今天细读《村治》二号先生给我的信,使我十分感谢。先生质问我的几点,都是很扼要的话,我将来一定要详细奉答。
我在“缘起”里本已说明,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,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。因为如此,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个根本的态度,便忽略了批评对方理论的方面。况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讨论会的宣读,故有“太简略”之嫌。
革命论的文字,也曾看过不少,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。先生所说,“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,诚亦未必悉中情理”,我的意思正是如此。如说,“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”,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?如说,“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”,试问张献忠、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?今日冯、阎、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?
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,稍一翻看历史,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。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,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?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,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?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,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?
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,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。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?此中“症结”究竟在什么地方?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?
先生要我作历史考证,这话非一封短信所能陈述,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。
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,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。在革命的状态之下,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,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。
大旨如此,详说当俟将来。
至于“军阀”问题,我原来包括在“扰乱”之内。军阀是扰乱的产儿,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。处置军阀——其实中国那有军“阀”可说?只有军人跋扈而已——别无“高明意见,巧妙办法”,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,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。
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,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,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。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,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,自身已失掉其依据,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,故不复能澄清政治,镇压军人了。
先生说:“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”,此言颇不合史实。军阀是扰乱的产物,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。二十年来所渭“革命”,何一非文人所造成?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,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?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,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?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。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,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?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,所谓政府,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,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。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,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。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,似乎不太过罢?
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,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。故先略述鄙意,请先生切实指正。
胡适。十九,七,二十九。